本篇文章4977字,读完约12分钟
郑少雄/文
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冬天,我独自在中国东北旅行。清晨,在从黑龙江省四等站绿岛开往牡丹江的区间列车上,硬座车厢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草味和肆无忌惮的脏话,这些来自男人、女人和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的南方口音阻碍了我交流的欲望,所以我只能半闭着眼睛听东北老乡的聊天。一位阿姨告诉邻居,她以4000元的价格卖掉了村子里的房子,打算搬到一个县或镇上。她的邻居向她表示祝贺,并对她的房子还没有被卖掉感到愤怒。虽然我脸上没有表情,但我的心已经在动了:什么,你在开玩笑吗?祖屋可以卖吗?20多年过去了,这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我和人类学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文化冲击来自我在华南的生活背景。在我的家乡莆田,我不想说祖屋神圣不可替代。祠堂、村庙、祖坟和宗谱都在大规模重建过程中。丁革命前,莆田人有下南阳的传统。改革开放后,他们也四处流浪谋生。然而,一旦他们发了财,第一件事就是花钱在他们的家乡建一所房子。一座矗立在故土上的像样的房子承载着泰国莆田人的生命意义。东北人似乎已经放弃了这个意思。

就妇女吸烟和骂人的普遍程度而言(以我童年的生活经历,农村妇女公开吸烟和责骂妻子是极其罕见和不合理的),特别是就她们对祖屋的态度而言,东北人和华南人几乎不是同一个民族。我当时的看法似乎被今天的学术研究所证实。什么是华南?首先,中国南方是弗里德曼笔下的边疆氏族社会。第二,根据今天南华宗的普遍共识,南华宗的兴盛并不是因为皇帝的高天高地远,而是明清以来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勾结的结果。宗族有效地整合了中国南方的政治生活世界,沟通和平衡了国家与社会的差距。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和民间宗教率先在华南复兴。然而,从汉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严云祥笔下的下角村,如果说它是东北农村的一个缩影,那它与华南社会是截然不同的。礼物的流动(以下简称“礼物”)表明,在东北农村,宗族几乎完全不存在,但姻亲甚至非亲属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在《私人生活的变化》(以下简称《私人》)中,由传统地方组织的衰落和国家权力的退出所导致的真正的空国家是,组织、结构和关系不再具有社会学意义,而是男女自由和欲望的自由,这构成了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东北农村生活世界的驱动力。简而言之,根据我的阅读理解,华南和东北的区别是氏族和婚姻的区别,制度和个人的区别,正统和非道德的区别。

杨念群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的理解。这是他第一次把莆田作为对质的案例,并与下角村并列。在评论严云翔的作品(私人和国家在亲密关系的变化,阅读,第10号,2006年)时,他提到,他看到了一个热灯笼旅游和一个振奋精神的郊游基于村联盟在莆田农村,包括学校儿童的参与。如果说在中国东北出现了道德衰落和个人没有公共道德的情况,那么莆田宗族价值观的复兴几乎可以看作是当代集体价值伦理崩溃的一种拯救。当然,不管神的威慑力在中国东北是否仍然有效,杨念群其实有无数的心。

礼物流动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
海外汉学人类学还有另一幅中国地图,这可能部分与斯金纳对中国经济地理的划分有关。例如,东北地区可以大致归因于华北板块;福建是中国南方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我也将遵循这一习惯,以便为那些局限于当代行政区划、也被困在今天的地图大炮中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些新颖的海外视角。

《礼物》(英文版)于1996年首次出版。从1971年到1978年,闫云祥作为一个归化的盲流在夏彤村生活了七年;在1989年重访该村并进行实地研究后,这种情况又持续了7年。这种独特的半局内人体验在海外汉学人类学领域是罕见的。这本书分为九章。在引言中,他讨论了理论对话的对象。由于其与商品相反的性质,礼物是西方人类学的经典话题。关于礼物的核心问题包括:为什么接受者必须归还礼物(也就是说,互惠对于社会维持的重要性)?给予者相对于接受者是否建立了有利的社会地位(社会控制和组合理论)?第2章是现场位置的概述。历史不到200年的移民村落和满汉混居的特点决定了夏茂氏族的不发达;第三章根据当地人的分类列出了21种送礼行为;第四章和第五章描述了礼物在农村的各种社会功能,特别是维持旧关系网和开辟新关系网的重要性。第六章论述了中国北方农村用来调节互惠原则(人情理性取向)内部冲突的地方伦理体系:人情。这些包括触摸和脸,这是人类情感的道德面孔;同时,人类的情感并不排斥他们的情感取向。第七章重点描述了中国社会中一些反向的、单向的礼物流动,即礼物从较低声望和权力的群体流向较高的阶层,而不期待回报,如孝顺或逢迎的礼物,这与中国社会等级森严和资源垄断的特点有关。第八章转向农村最常见的礼物交换形式:彩礼和嫁妆。通过历时性的材料分析,指出彩礼和嫁妆已经从两个家庭之间的礼物交换转变为代际财富再分配。这种转变响应了更广泛的社会变化,新来者的主动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这也为下一本书奠定了进一步的延伸线索。

综上所述,虽然《礼物》也涉及到个体欲望和行为者的特征,但它的立足点主要是在华北农村道德原则、关系网络和社会规则的结构生成和演变上。它的贡献不仅在于用本土经验挑战西方人类学的礼物理论,还在于从礼物交换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状况。首先,它指出互惠本身根植于潜在的文化矩阵,互惠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变化,甚至在同一文化的不同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互惠缺失的现象;第二,发现二元商品关系和礼物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中间形式,如走后门的工具性礼物赠送,其实质是礼物的商业化导致了商品交换的人格化,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洞察,表明华北农村正在经历社会主义再分层的历史转型;第三,强调华北农村礼物交换中的情感因素,这与欧美社会的礼物没有什么不同,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华北农民人格的完整性。

私生活的变化及其后的自我怀疑
严云翔在《礼物》中注意到,结婚礼物的交换应该发生在两个家庭之间。然而,当年轻人结婚时,他们被分割为一张通行证(不管他们的兄弟是否未婚),彩礼被转换成现金并直接交给新娘(而不是新娘的父母,以免被转移到她姐夫那里去娶她的儿媳),这对夫妇总是尽可能多地争取彩礼和嫁妆。这一事实表明,在婚姻中,礼物交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财富继承,财富继承是提前发生的,并指向新来者。严云翔将其归因于年轻人自我意识的提高。即便如此,严云翔还是公正地写道:虽然新郎和新娘一样,都渴望夫妻独立,但他们不敢带头在婚姻交换上讨价还价,也不敢带头提出要离开父母的家。为了赢得高额彩礼和直接补贴,通常是新娘代表夫妇扮演一个自私和强大的抗议者形象。这一战略举措仍然源于家族组织中纵轴的残余影响。它仍然支持父母对儿子的权力和威严。《私人》(英文版)于2003年出版,比《礼物》的第一版晚了7年。在2005年中文版的自我叙述中,严云翔谴责那些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人往往表现出极端功利的自我中心取向,在坚持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他人的支持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华北的年轻人发生了什么?

《私人》是一本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的书,它的民族志描述和理论分析非常吸引人。引言部分展示了作者的理论和方法论抱负,即在现有中国家庭研究合作模式的基础上,突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北方农村家庭的个体因素和私人取向。第一章从社区视角、公共生活的沉浮以及村庄的宗族组织和社会网络等方面总结了村干部和国家的作用。第二章和第三章,在不断变化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考察了50年来下跳村择偶过程中的自主化和浪漫化趋势,以及这一转变过程的诸多细节。第四章描述了家庭关系的结构变化。夫妻轴心取代了父子轴心,成为家庭中的主导关系,父母的权威下降,妇女的地位上升。第五章考察了居住模式的变化,即家庭空的更新与家庭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导致家庭生活隐私和家庭内部个人生活隐私的双重后果。第六章分析了家庭财产分割的各种方式,包括早期分割、系列分割、彩礼交付和支配。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父权制正在衰落,这也是新时期官方意识形态不断支持的结果。第七章探讨孝道与养老危机,以及中老年人对老年的担忧和防范。作者指出,这与官方意识形态(包括法律)内部的矛盾、国家的经济剥夺、市场化的逻辑以及信仰和道德世界的崩溃密切相关。第八章论述了由于孝道和养老模式的改变,农村自觉的计划生育观念和基于理性选择的生育文化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严云翔关注的是当代华北村落中的爱情、家庭和代际关系等新现象。他认为家庭生活私有化的倾向日益突出,代际关系中的亲密关系和责任伦理不断下降,年轻个体的情感、欲望和自我决定不断上升。一方面,国家在集体化过程中剥夺了家庭原有的社会功能,改变了农村的道德世界,将分散的小家庭和个人直接纳入现代体系;另一方面,去集体化之后,随着国家在私人生活领域的退出(当然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剩下的空空间被市场、商品和全球消费文化所占据,这催生了一种没有公共道德的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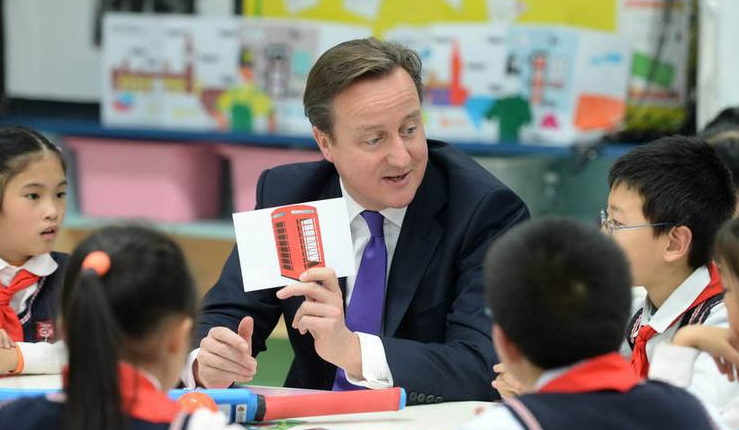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自然。令人惊讶的是,十多年后,严云翔开始怀疑自己的核心结论。他问自己:是世界变了,还是观察视角有问题?在近年的公开演讲中,他不断调整自己的结论,他的集中思考体现在《美国人类学家》去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第118卷第2期《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和下降的家庭主义》中。他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成年子女与父母实际上已经分离,但由于第三代的教育需要,三代人在日常生活中被重新组合成一个准家庭或隔代家庭,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情感关系。实现亲密关系的途径是夏密人对孝道的重新定义:年轻一代的幸福已经成为长辈的内在追求,年轻一代不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和屈从于长辈,即所谓的孝道是不顺利的;第二,媳妇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第三,它故意混淆了亲密和隐私之间的界限。代际亲密伴随着一种被称为向下家族主义的现象。所谓向下的家族主义,也就是严云翔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新家族主义,是指家庭中资源的分配、情感的亲近以及野心所指向的目标,从向上荣耀祖先到向下期盼成龙。

为什么年轻人在新世纪后会突然重新加入回归家庭?严云翔认为,这绝不是中国北方农村地区个人化进程的逆转,而是源于各种社会压力和社会因素:1。年轻人离开家庭后,他们找不到其他身份;2.城乡移民、城市化和风险社会使年轻人回到原籍家庭寻求信任和支持;3.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使两代人的情感相统一;4.独生子女政策促使老年人增加对年轻一代的物质和精神投入,这导致了代际关系的情感化。但不管怎样,年轻人在生活的训练中很快成熟,他们变得更加感恩,从而通过父母的战略合作重塑了代际间的亲密关系。总之,严云翔想说的是,在中国北方农村的个体转型中,西方个人主义找不到它生长的土壤。

厦门与莆田的共同危机
闫云祥自己的战略撤退有些令人困惑。这种战略退却意味着他在《私人》中正确地指出,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是残余的传统文化、激进的社会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最近的思考中,他试图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解释年轻人的温情回归。在他看来,指责一个没有公共道德的人似乎太尖锐了。在中国北方农村的个人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现代性,是一种关系定义下的个人/人格,它必然在家庭和集体中获得意义。通过这次战略撤退,闫云祥可能成功地平息了公众的反抗。然而,尽管回归的家庭更多的是受实用主义的驱使,但我相信人类学家仍然不能轻易置身事外,如果我们重温一下范跑跑、肖月月,他曾经关注的粮食危机,以及摸瓷、瞎井、莆田一些医院等现象。

是的,我不幸又提到了普天。与新教伦理不同,另类现代性的概念必须植入人类学家(包括我自己)和从事或关注莆田乃至华南的历史学家的心中。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在中国南方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南方不仅面临着未来的挑战,而且还承载着习俗和人们的情感,包括在社区或社会中用美德教育和培养现代主体。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杨念群作品的典范,沿海的邹鲁和传统资源如此丰富的名邦,即使莆田人在他们的村庄里渴望公共的正义和慈善,当他们步入陌生的社会,只要像莆田科医院这样的公共形象呈现在外面,莆田似乎与新世纪前的下海角村没有什么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道德??这种言论应该放慢速度,所以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我们一起探索一条更合理的道路。
标题:变革中国,公德危机解除了吗?
地址:http://www.aqh3.com/adeyw/11098.html

